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
郭永玉教授:
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晚上好!今天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,因为它是一年中很普通的一天。但是,对于我们心理学院来讲,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,因为我们迎来了著名学者邓晓芒教授。邓老师到华师来过好多趟,作过多场报告,尤其对于文科院系的同学们来讲,可以说邓老师就不需要介绍了。但是,对于我们心理学专业的同学来讲,可能还要简单介绍一下。邓老师是康德研究的专家,他直接从德文翻译了三大批判,这是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;另外,写过影响很大的康德研究的专著和论文。但是,邓老师又远不止是康德研究专家,因为他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,特别是黑格尔,所以,邓老师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。
但是,邓老师又远不止是德国古典研究专家,他对整个西方哲学,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。而且,我还可以说,邓老师又远不止是西方哲学史的专家。他对东方,特别是中国、中国哲学、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对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。因此,邓老师其实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、文化学者。所以,我想,对于邓老师的学术头衔、称谓,最恰当的就是邓老师是个真正的哲学家。这是我对邓老师的认知。邓老师这学期到我们学院来,开一个系列讲座,讲座的主题是中西文化心理比较。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很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,那么他的思想对于我们心理学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启发价值的。应该说今天是遂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。我是从2000年正式拜邓老师为师,这个心愿到今天实现已经过了八年。这个讲座我们计划是一共十五讲,今天是第一次。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请邓老师为我们开讲。
邓晓芒教授:
刚才郭永玉老师说的有些过奖了。我搞的研究范围比较广,但实际上呢,都是停留在还未进一步深入的这样一个水平。当然有些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,所以在国内中西文化的比较这方面,也有些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,也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议。那么今天开始这个系列讲座,就是关于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,是我关注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话题。我今天打印的这个稿子,是根据1988年的一个初稿。1988年我在第一页上面还写了,就是从2月14号开讲,到今天已经21年了,讲过8次,当然作了很多修改。因为,毕竟二十多年了,有些思想有所改变,有所发展,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历程起了很大的变化。但是,基本的思路、观念、框架都还是与那时候一脉相承的,也就是说我对中西文化心理比较有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看法。那么,今天我主要是想就这样一些想法,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,这样一个构架,给大家做一个介绍,这是我多年以来研究的一些心得。于丹不是讲“论语心得”、“庄子心得”吗?我也是一种心得。但是,我和于丹不同的是,我还是比较深入到原著以及后面的思想,而且是中西对观,把我所研究的专行——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里面所体现的文化精神,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加以比较。加以比较当然不是要比出个高低,来满足某种自尊心,或者是要打击某种倾向,目的倒不在于这里。而是要把现状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揭示。当然里面会有一些倾向性,我的基本倾向性还是继承“五四”以来形成的传统。当然对“五四”的传统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传统我都有反思。那么今天所要讲的,我想首先是一个简短的序言,然后呢,开始第一讲。序言呢,就是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(板书)。
我一般不喜欢做图文(PPT)软件稿,我喜欢要么就是空口讲,要么就是做点板书。我觉得图文(PPT)软件稿把人的注意力从语言本身引向了文字和图像,我主要是希望听众能够注意我的语言和表达。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其实是不用说的。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?处在一个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。不管你是高兴呢,还是失望,你同意还是拒绝,我们现在正在走,所以中西文化的冲突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冲突。一切冲突最后都要归结到中西文化的冲突,中西观念的冲突,乃至中西文化心理的冲突,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的,不光是国际上的冲突,而且是我们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,最主要、最关键的冲突都与这个有关。
所谓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就是说的我们这个时代。李鸿章说过这样的话,曾国藩、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,还有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们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从1840年以来,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历程。从历史上来看,首先是洋务运动,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。洋务运动是中体西用,他们学习西方的,主要是它的“船坚炮利”。那么中体西用,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,这条路看来走不通了。于是又有一些反思,主张不是外在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解决问题,而是要学习西方的制度。于是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搞了戊戌变法,但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,制度变革失败了。失败了没办法,就反对晚清统治的革命,导致了清朝垮台。清朝垮台以后还要学西方,这时候,就开始深入到学习西方的观念,从外在的物质层面、制度层面进入了观念层面。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就开始了国民性的反思、国民性的批判。李泽厚讲那时是“启蒙和救亡的双层变奏”。有的人不太同意这种说法,但是,这是一个事实,当时讲启蒙就是为了救亡。在这样一种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过程中,逐渐地产生了一个启蒙的果实、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?就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。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被我们看做是“五四”启蒙的结果。如果说有什么结果的话,那么很明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胜利。“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”,这样一种说法,就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启蒙的果实当做救亡的工具。所以李泽厚又讲“救亡压倒启蒙”。救亡压倒启蒙是必然的。因为一开始,你就把启蒙当做是为了救亡。那么,在启蒙中我们发现能够救亡的就是马克思主义。孙中山也讲联俄联共,因为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,最具有号召力,最具有启蒙意义,而且最具有达到救亡效果的一种功能。但是,这样一种把启蒙当做救亡的工具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,而且是从苏联,从列宁、斯大林,特别是斯大林传来的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,当我们把它中国化以后,掩盖了一些国民性的深层次的基因,这个是被我们所普遍忽视了的。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,是所谓儒家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,实际上里面包含着国民性的、传统的一些基因。这些基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被人注意,我们认为是崭新的,其实是新瓶装旧酒。里面有很多旧的东西,已经有很多人对此作了分析。比如说农民起义的色彩非常浓厚,延安当时演的一个京剧《逼上梁山》,就跟这个梁山起义差不多。
从1949年以后,经过了几十年不断地演变,不断地搞运动,启蒙的那些价值一步步地被清除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步一步地加紧肃清西方的思想。在我们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里面,这种传统文化的基因,越来越显出它的排外功能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展到顶峰。于是“五四”启蒙已经达到的成果,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候可以说丧失殆尽了。当然有的人说还有苏联来的东西,那个根本不是启蒙的东西。苏联的一套体制,一套阶级斗争,我们以为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,其实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,你想想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那些斗争,哪一个是阶级斗争?根本不是阶级斗争。不管是文化革命的武斗,还是对走资派的斗争,都不是阶级斗争,都是思想斗争。阶级斗争是思想斗争吗?我们讲“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”,其实根本就不是阶级斗争。阶级斗争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,不是由思想决定的,所以我们搞的是思想斗争,而且是人事斗争、权力斗争。所以“五四”已经达到的那些成果,包括近代以来的成果,全部丧失,蒙昧主义达到顶峰。
所以,我们要谈中西文化心理比较,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,就是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了解。我总认为,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个未来几十年到一百年之内我们摆脱不了的话题。我们沉睡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噩梦中还没有完全醒来。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反思,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像目前的这样一个水平,就是归结到某一个人,归结到某一个领袖所犯的错误,他为什么犯错误、他的个性怎么样、他的道德水平又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些反思都是很肤浅的、层次不高的,当然也是必要的。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反思尤其必须要反思到群众文化心理,而不是哪一个人。哪一个人振臂一呼,群众要能够响应啊。你之所以振臂一呼能够起作用,就是因为你掌握了群众文化心理,才能够起作用。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,他掌握了百万红卫兵的心理,不光是红卫兵,包括教育那些红卫兵的老师和家长。他掌握了群众文化心理,才能发动起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那么,我的反思呢?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过,“文化大革命”里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最主要的特色:一个是痞子文化的特色,一个是纯情文化的特色。痞子文化大家知道,毛泽东早年关于痞子运动就有一个高度的赞扬。他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(1927)里面,对于农民的那种痞子行为大加赞扬。为什么赞扬?为什么他赞扬了以后很多人都感到痛快?连那些深受其害的人、旁观者,都觉得他说得对,就因为这种痞子恰好表达了一种纯情。我们今天讲纯情好像是一种很高雅的东西,琼瑶啊、汪国真啊,这些人都是纯情的诗人、纯情的作家。但是他们所表达的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面。纯情之所以纯,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本来的模样,回到了本心,它没有遮掩、没有虚伪、没有做作。那么,最没有虚伪、最没有做作的呢,就是那种最没有教养的,那就是痞子,痞子是最没有做作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流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“我是大老粗”,工人阶级、贫下中农都自我标榜:我是大老粗。我家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学。我家里三代讨饭。这是最红的,叫做“根红苗正”。他们对于党、毛主席是最纯情的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里面他们是最痞的,是最能够冲在前面的。出身“红五类”的那些红卫兵,是最能够充当打手的。这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才兴起来的一个东西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结构。就是说最纯情的东西就是那种最自然的东西,最自然的东西就是那种最没有受过教育的,最没受过教育的那就是痞子。那么这种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王朔的小说里体现得很多。实际上你不要以为王朔的痞子文学讲的是那些流氓恶棍,他讲的那些痞子都是非常纯情的小痞子,不是真的要害人的那些痞子。他们都是出自纯情,有真情啊。痞子面貌底下有真情的人,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所以,王朔也能够写很纯情的小说,像《过把瘾就死》、《空中小姐》啊,都是很纯情的小说。但他也可以写很痞的小说,《千万不要把我当人》就这样一种小说。那么这两种文化——痞子文化、纯情文化,它们具有同一性。这种同一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为一种反文化的文化。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高度的。应该承认,像《红楼梦》里面描绘的——那种奢侈、那种生活的享受、那种细腻、那种高要求,那是高度的文化。但是,这个文化骨子里是反文化的,就是最高的其实还并不是外在的奢侈,而是内心的清高。内心的清高就是要回到本性,回到本性要把这一切都抛弃,要把这种荣华富贵都抛弃。最后贾宝玉出家嘛,抛弃一切人间荣华富贵。所以《红楼梦》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层次,同时也表达了最高的层次必然走向灭亡。为什么一治一乱、改朝换代,文化一旦发展到高雅,经过农民起义,马上又跌为蛮痞?这里面有这个文化结构的基因在起作用。所以我认为是一种反文化。
那么,在这个文化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是必须注意的。一个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天和人是合一的,也就是自然和人的合一。人就是自然的,自然而然的,而自然也是带有人性的,天人合一;再一个是“诚与天道”,这是儒家主张的“诚”,真诚,诚心诚意。诚信与天道,“诚者,天之道也”。你只要诚,你就可以达到天道;第三个是“赤子崇拜”,崇拜赤子之心,我把它称之为赤子崇拜。中国人通常崇拜赤子,不管儒家、道家、佛家,都崇拜赤子,就是刚刚生出来、赤条条、没有经过任何文化的教养、没受过训练,就是一颗本心、一颗真心,这是最高的,赤子崇拜;第四个是“难得糊涂”,当然这个是从禅宗来的,但实际上在老庄那里已有,反智主义;第五个是“无私无我”。无私、天地无私、无我、无为这些观念,体现出来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。当然其他的文化里也有,但中国文化表现得比较突出的,一个是自欺,自欺导致伪善,这个是鲁迅特别讲得多的。用瞒和编造出种种逃路来,不愿意正视,自欺和伪善;第六个还有怀古、念旧。总是怀念古代,三皇五帝、大同世界,想回到过去;第七个是权力至上,崇拜权力。中国人特别崇拜权力,因为他没有超越权力之上的任何其他的追求目标。在西方有个宗教,它是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。那么中国呢,缺乏这个层次。所以权力就是我的宗教,谁当权,我就喊他万岁。权力至上,那么由权力至上导致的逆来顺受,以众凌寡,欺软怕硬,对上司一副面孔、对下司一副面孔,奴性,这些都来了。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关键词。
那么,所有这些形形色色,能不能归总一下呢?所有这些问题,西方也有,也都可以找到。那么我可以把它归结为缺少两个精神:一个是理性精神,一个是自由精神。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缺乏,导致了中国文化心理的这样一些特色。当然,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也都需要理清:到底是什么含义。我在后面讲课的时候呢,会专门把这些话题来澄清。因为它有歧义,自由啊、理性啊,这些都带有歧义的。“五四”启蒙提出了一个口号,就是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就是我刚才讲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一种表现。但是,“五四”的时候提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没有着重从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这个层面上谈。一般来说呢,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要有看得见的效果。“德先生”就是民主。西方人体制跟我们不同,他们是民主制,当时的中国是专制;“赛先生”呢?西方人讲科学,科学带来了技术,这是很明显的。当然“五四”跟洋务运动已经不一样了,跟戊戌变法也不一样,他们深入到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是一种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,已经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来找根源,来寻找学习的对象。但是,他们只是从抽象的观念层面提出了改造中国文化的使命,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的内部,所以还是比较表面的。虽然是从精神上、观念上来讨论这些问题了,已经意识到我们传统文化心理方面有毛病。不光是制度的毛病,也不是我们技不如人、我们的技术被人打败了,而是我们的整个传统文化心理、国民心理、国民性里面有毛病。但是,还是比较表面的,着眼于外部效果。
这里面唯有鲁迅可以说是个例外。鲁迅已经看到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后面还有东西。所以,鲁迅对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反倒不是很感兴趣的。他早年还批判过,说民主就是开国会嘛,开国会就是多数压制少数,少数服从多数,大家投个票,那就是多数压制少数,他主张“尊个性而排众数”。所谓科学、科学救国,就是办实业嘛,办实业就是大家发财嘛。他的主张则是“培物质而张灵明”。鲁迅当年在《文化偏执论》里面曾批判过这两种倾向。但他自己也没有拿出更好的东西,他只不过是深入地看透了这样一种时髦,“德先生”也好,“赛先生”也好,拿到中国来,就变成了某些人牟私利的一种旗号。而鲁迅所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,当然就涉及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后面的两个东西:一个是理性,一个是自由。“德先生”后面其实是自由精神,而“赛先生”后面实际上是理性精神,你光讲科学和民主,你不讲理性和自由,这个层次还不够深,还不够深入。所谓民主,无非就是科学的自由、理性的自由,用理性来规范人的自由,使人的自由达到最大限度。用理性的方式来设计一个社会制度,使得每个人在这个制度底下,都能够充分地发挥这些自由,这就是民主,这就是自由精神。那么“赛先生”呢?无非就是自由的理性,科学,有科学精神在它后面,那不是科学技术。这一点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。我们今天讲“科学发展观”,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技术,就是重视科技。“科技”是一个含混的字眼。科学精神实际上是要自由地进行理性的思考,进行科学研究。科学如果没有自由是不行的。科学如果拿来为专制服务,那是不行的。希特勒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。希特勒也有科学啊,但是在专制之下,科学发展不起来的。这些科学家纷纷出逃,为专制服务的那些科学家也提不起精神。他歪曲了科学精神的本来的性质。但是,毕竟鲁迅先生他太孤单。他以一人之力,无力对抗整个国民的性格。所以鲁迅一生没有人理解他,也没有人支持他,大家都在批判他,都在批评他,包括那些左派知识分子。而且鲁迅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国民性的毒。他自己讲:“我自己深中了传统的毒。”他自己也深中了传统的毒,比如说老庄和韩非。他明确提出来中了韩非和老庄的毒,韩非就是法家嘛,就想要用一种急功近利的严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所谓国民性的问题、文化心理的问题,不能够那么着急的,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。鲁迅当年认为在他这一代,或者顶多再过一代,就可以解决国民性问题。鲁迅当年太急躁了。再一个老庄,就是太随便。搞得没办法了他就随便,就是“无可无不可”,就失去了他的目标。
那么,我们今天有必要做更深层次的反思。我这里讲的,主要是要通过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,来理清西方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真正含义、深层次的含义以及它的全面丰富的含义、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含义。比如说在知识方面、在道德伦理方面以及在审美方面,甚至在宗教意识方面,如何表现出理性和自由。西方的理性和自由,还经过了宗教意识的这样一种锻炼。西方有宗教意识,而我们中国人非常不屑于谈宗教。基督教信上帝,我们觉得那是蒙昧,那是落后,那跟启蒙是沾不上边的。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呢,基督教在形成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方面其实是功不可没的。我这里要给它做一点翻案。
那么,理清了这样一些含义以后,我们就更容易看到:中国传统恰好是缺乏这两大精神要素,这是我们的真相。看破了这样的真相,我们就可以去寻求救治的办法。当然,这个还是鲁迅提出来的一个使命——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,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,就是改造国民性。那么,在心理学方面,就要根据不同的对象,来把握不同的心理结构。比如说西方心理学。我们现在的心理学,基本上是西方心理学的构架,大框架是这样引进的。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。西方心理学,包括现代当代的很多心理学,他们都是西方人的心理、西方白种人的心理,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不同,不能搬用、不能套用。不管是弗洛伊德也好、格式塔心理学也好,这些东西都不能套用的。你简单地套过来就很可能出错。所以在心理学的学科方面,我们通过这种比较,也可以为我们创立中国特色的国民心理学,打下一点基础。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一讲。
(讲座开设于2008年秋季学期,转载自《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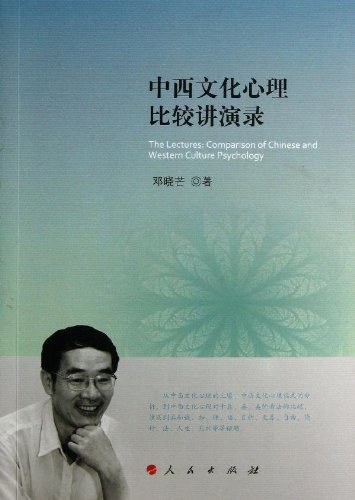
目录
原文链接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1vrzymOypxkWD4DpWPTkA
编辑 |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
